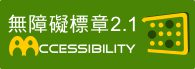韓劇《機智住院醫生生活》描繪四位住院醫師的情誼與臨床日常,引發觀眾共鳴。但在現實中,醫學生從醫學院畢業後,尚未進入專科訓練前,必須先完成兩年的「一般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 PGY),成為不分科住院醫師。這段期間,他們尚未選定專科,得到每一科輪值,汲取不同老師的經驗,面對不同病人、病情與團隊,學習每一個臨床現場的節奏與挑戰。相當辛苦,卻是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醫師」的一個重要過程。
◎最好的止痛藥──傾聽
那是一名46歲的女性患者,因為長期憂鬱症和下背痛,導致長時間依賴嗎啡止痛,這次她因為急性腸胃炎住院,但感染控制穩定後依舊反覆喊痛。為避免嗎啡成癮,醫療團隊嘗試以各種方式減藥,令人困擾的是,她不是個會遵從醫囑的人,過往在其他院所,便已有囤藥的習慣,只要覺得不舒服,就自行加量,甚至平均每一到兩個小時就吵著要止痛藥。
照顧她的是PGY醫師吳汶珊。那天值班時,她又開始喊痛,可是嗎啡已經到達使用上限,無法再開立更多藥物。左思右想,吳汶珊決定換個方式。她空手來到病房,搬張椅子坐到床邊,開口詢問:「你今天吃了什麼?」「誰買給你的?」……
一問一答間,對方放下戒心,慢慢說起心裡話。原來,跟年邁母親同住的她,很早就跟社會脫節,生活圈非常狹窄,在學業跟工作長久碰壁的壓力下,無助跟無望儼然變成生活中另一種形式的疼痛。吳汶珊靜靜聽著,說到激動處,病人流下淚來,但意外的是,整個過程中,她沒有要求要吃止痛藥,只在最後跟醫師說了一句:「謝謝你沒有把我當成一個神經病。」
「那句話我永遠記得,那不只是一句感謝,更讓我知道她要的是有人願意當她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病人。」從那天起,團隊改變方式,護理師牽起她的手鼓勵下床,藥師耐心地討論怎麼將藥物減量,考量患者食慾不佳,營養師們從願意吃的食物開始,一點一點鼓勵她多吃一口。她也越來越健談,從年輕時的夢想聊到對重回社會的渴望。
吳汶珊提及,藥物減量不可能一蹴可幾,但自己會在對方討藥時鼓勵:「給自己的身體一點時間,就像本來完全不想進食的你,今天吃了一碗稀飯,只要還在能夠忍受的範圍,身體會慢慢適應的。」病人對嗎啡的需求程度降低,這個過程讓吳汶珊體會:「如果單看病歷上的用藥紀錄、喊痛頻率,或許會覺得這是一名很難搞、依賴性很強的人,但當我們真正用心聽她說話,會發現她是在告訴我們──她多麼希望想活下去。」她感謝這次經驗讓自己學會照顧一個人,而不是處理一個病,她感觸甚深地說:「醫療的本質不是要病人乖乖地按照醫囑去做,而是醫療人員願意打開耳朵,聽見他們內心的聲音,成為病人心中微弱卻重要的光。」
圖說:吳汶珊到病房關懷病人與執行醫療業務。(圖/范宇宏)
◎留給病人的溫度
還不是專科醫師,卻已經站在臨床第一線。PGY醫師離開學校的保護傘,必須主動觀察、訓練思考,看見病人的需要。這樣的成長軌跡,同樣印證在另一位PGY醫師易烈瑜身上。
「剛到內科時多了很多任務,讀書、運動的計畫兩頭空,每天像無頭蒼蠅一樣團團轉,回家累到什麼都做不了。」易烈瑜回憶,當時,她在教學部劉子弘副主任的引導下,透過「ILP」(Individualized Learning Plan,個別化學習計畫)替自己下了兩個目標,一是時間管理,二是熟習放置中央靜脈導管。設下學習目標後,主治醫師即在臨床上給予大量放置導管的機會,讓她得以實際操作。易烈瑜也在老師的經驗分享建議下,試著把同類型的任務集中管理,熟習作業流程,讓生活逐漸找回平衡。
技術效率的提升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仍是醫師養成不可或缺的一環。易烈瑜提起一位在急診遇到的患者,因為重度憂鬱症的緣故,她有嚴重的自殘習慣。那天,朋友取消了約會,情緒崩潰下用美工刀割傷自己,來院縫合。處理傷口時,易烈瑜跟她聊了許多事,對方說:「我試過轉移注意力,紀錄傷害自己的間隔天數,把這個當作目標來努力,但是我又失控,又讓家人擔心了……。」看著情緒非常低落的眼前人,易烈瑜鼓勵說道:「沒關係,雖然要從頭算起,但每一次比前一次更久一點,就是進步。」聞言,病人露出了笑容,誇獎醫師到:「你縫得真好。」
她是易烈瑜記憶中特別且難忘的病人,不僅僅是因為這句誇讚。易烈瑜認為,相較一般急診患者常有的情緒激動、態度急躁,這位病人雖然有身心困擾,但本性相當體貼,這也讓原本只要把傷口縫合就好的她相信,有些人的創傷或許無法根治,但多付出一點傾聽與關心,就可以給他們更多的能量,畢竟,醫師們多講的一句話,都可能在病人心裡留下溫度。
圖說:易烈瑜與劉子弘副主任討論自己的學習計畫(左);到臨床照顧病人(右)。(圖/范宇宏)
◎最難的一課──為自己負責
要開始替自己所做的判斷和決定負責,吳汶珊坦言,在內科輪值的時候最為崩潰,加上時逢年節,病人多樣化、人力又不足,曾經一整天都在處理疑難雜症。夜班的疲憊感以及三不五時的教學課程、跑病房、寫病歷,幾乎沒有喘息空間。「睡眠不足的情況下做判斷,可是臨床歷練不足,僅能依靠過往課本的知識來決定,令人更容易焦慮,但也只能先做再說。」她說,在事情塵埃落定得以喘息時,想哭、想放棄的念頭才會如排山倒海而來,「但是還是得面對,繼續學習、詢問、累積經驗,因為我還是希望能用自己所學讓他們好起來,出院後就不要回來了。」
抱持一樣的責任感,在大學時便接觸過醫學教育的易烈瑜提及,學習應該是以自我為導向的,要知道自己缺什麼、需要什麼,並且主動去找答案,而不是等著別人餵食知識。這樣的認知在進入臨床後更為明確,沒有老師手把手的教學後,端看自己是否有能力將所學運用到病人身上,但凡缺漏,便要自行想辦法努力補足。未來要走眼科的易烈瑜深知自己的個性無法變成跟患者天南地北聊天的醫師,但她期望自己多做一點衛教和提醒,讓病人感受到溫暖。
從「學生」轉變成「醫師」,是心態的調整,也是責任的轉移。訪問過程中,兩位PGY不約而同地提及,學習路上所遇到的老師都有著不同的風格,即便步調不盡相同,但都是他們在「人醫」路上,成為能獨當一面醫師的重要養分。
(文/廖唯晴)